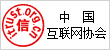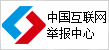|
男团火了,国内偶像女团仍在困境中找出路 男团竞演养成类真人秀《偶像练习生》和女团青春成长节目《创造101》的相继播出,让观众持续将目光聚焦在职业偶像及其背后的产业上。 相比于近期因节目出道,势头大好的男团,女团似乎面临着更多问题,毕竟《天然生成是优我》《蜜蜂少女队》《加油!美少女》《夏天甜心》等一系列的女团养成节目并没有成功地推出一个真正爆款女团。 为此,新京报记者专访多位业内人士,详细解读女团背后的艰辛与出路。 偶像 精神安慰、心理投射,但接受度有多高? 2011年秋天,王一凡去东京大学读研。彼时,关东大地震的余波还在继续,大小余震不断,人们在忐忑和焦虑中度过每一天,不知道自己所处的土地明天是否依然完好无损。身处其中的王一凡,真切地感受到了这种低落,在那样的氛围中,正是AKB48那群蹦蹦跳跳的小姑娘,给了人们极大的精神慰藉。王一凡描述了他当时在电视中看到的场景,AKB48的成员去东北震区演出,唱着欢快、青春的歌曲。台下的孩子们跟着小姐姐们一起唱歌一起笑,他们带动了周围的大人和参与救援的官兵,所有人笑完之后就开始哭。“那种精神震撼力是非常强的。” “如果没有大地震,AKB48能成星,但不可能有现在的地位”,被这些现象吸引的王一凡,甚至改变了自己的论文方向,投入到对AKB48的研究中,2014年他回国参与到SNH48的运营中。之后又参与创办了少女组合IdolSchool。他觉得,AKB48在震后那种特殊环境中爆发的疗愈力,源自于反差。“在儒家文化圈的观点中,小姑娘总是弱不禁风的,所以她们在逆境中的拼搏,会更有感染力的。”震后那年夏天,AKB48曾经专门举办过一场赈灾应援演唱会,彼时由于地震的影响限电,处在高温中的后台无法使用空调,不少成员在表演时中暑晕倒,但没有人放弃,短暂休息后又继续演出。 即便没有天灾,偶像仍然能带来很多精神安慰。王费澌在决定加入女团之前,是标准的女团粉丝,喜欢日本另一个常青的女子组合早安少女。那时她初中毕业后赴美读高中,出发时还不满15岁,坐飞机都需要被托管。独自一人在美国,总有些难熬的时光,在这些日子里,女团中素未谋面的姑娘们给了她很多鼓舞,“她们都那么努力,为什么我不能再努力一下呢?”。 家中收集了一屋子女团周边的影子(化名)也有类似经历,2008年大学毕业时,他看日剧、听歌时关注到了早安少女。影子专门去看了介绍早安少女的幕后纪实纪录片,这群为了梦想努力拼搏的成员打动了正处于毕业迷茫期的他,“她们特别不容易,为了追求梦想能付出那么多。” 在张绍刚看来,偶像身上总是有粉丝的某种心理投射,有时是自己的成长历程,有时则是愿景甚至梦想。偶像作为被投射的客体,很难被替代。“比如说范冰冰,她的位置太高了,很少有人会在她身上看到自己。”张绍刚举例说。 刘勇和他的虚拟女团“And2girls安菟”是偶像市场的特殊存在。安菟由五个漫画形象组成,组合中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设和故事。一次,9岁的小侄女跟他说,不要相信网上那些关于偶像的言论,都有团队在背后操作。刘勇被惊到了,于是,他下定决心做一些能带来正能量的东西。在安菟的世界中,没有太多尔虞我诈,五个追梦的姑娘努力战胜各种困难,实现自我的成长。刘勇认为,可以一直保证人设和叙事统一性的虚拟偶像是引领青少年精神非常好的载体。“对他们来说,偶像说的话比其他枯燥的说教有用得多。” 偶像是粉丝的榜样,能恰到好处地鼓舞粉丝,“身边的人如果通过努力进步了,可能会有些嫉妒的心理,很难把他们当作榜样。”影子说。 并不是所有人都能理解这种榜样的效应,璐璐(化名)和小佳(化名)都是《女团》纪录片的编导,纪录片一上线,璐璐和小佳认真地看每一条弹幕,有些网友的留言让她们难过,一些观众讽刺粉丝们,甚至用不友善的词汇形容喜欢女团的男粉丝们。璐璐很不理解这种攻击,在她看来,偶像能带来的快乐是健康而无害的。 “漂亮姑娘在那儿蹦蹦跳跳,大家总会赋予它更复杂的意义,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人们不了解这种文化产品”,张绍刚解释说,但他旋即提出了一个新的疑问,“市场对这个产品真的做好准备了吗?” 风险 不能谈恋爱、想红靠机遇 决定正式加入SNH48之后,王费澌跟男朋友分了手,为了告别过去,她甚至重新换了一个微信号。多年之后,早已离开女团,即将从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毕业的她,说起这段往事,虽然觉得有些对不起当时的男朋友,却并不后悔这个决定。 “恋爱禁止”是偶像行业一条不成文的规定,2017年,在日本知名女子偶像组合AKB48的人气总选上,旗下组合NMB48的成员须藤凛凛花突然当众宣布结婚,一片哗然的除了粉丝,还有其他团员,团内前辈大岛优子直接在社交平台上炮轰了这种行为。 这个准则有不合情理的地方。艺人经纪品牌“中樱桃”的创始人张展豪运营着多个女团,做了9年艺人经纪的他坦言,偶像的培养和管理有些许违背人情之处,比如禁止恋爱、限制饮食等等。 主持人张绍刚把这些限制解读成风险,他前段时间参与了一档名为《女团》的纪录片的拍摄,跟着制作组走访了国内外女团的运营者、女团成员和家长,试图从多个维度找到“女团运营举步维艰”的答案。在他看来,任何一个职业选择的背后,都有风险,偶像也不例外。选择成为偶像,就意味着做好了承担风险的准备。 然而,偶像的风险,并不止于此。被视为顶尖偶像的鹿晗,在公布恋情后,引发了一场娱乐圈“大地震”,纵然有各种声音叫衰他的发展前景,但成为顶尖的流量偶像,已经是种成功。因为大多数人直至偶像生涯终结,都籍籍无名。“不努力一定没戏,努力了也不一定有戏”,不少业已成名的偶像们,也会将自己的成功归因于运气。 女子偶像面临的环境更为严苛,25岁被不少人认为是天花板年龄。余穬曾是偶像团体“蜜蜂少女队”上海二队的队长,这个从小学舞蹈,在上海外国语大学主修日语,还辅修了上海戏剧学院播音主持专业的女孩,大四加入女团后,就因为各方面的出色表现获得了公司的关注。但一年合约期满之后,余穬还是选择离开女团,转型成为脱口秀演员。作为团里的“大龄成员”,感受到了年龄带来的潜在瓶颈,是她离开的重要原因,她说与其在女团这个领域等待难以预知的机遇,不如去另一个生命周期更长,更容易通过努力带来好结果的行业。 家里有个一心想做女团的女儿,张楚寒的爸爸有着更多父母式的担忧。张父并不反对女儿以偶像为目标,父女俩的争执源自实现目标的途径。张楚寒加入了女团Hello Girls,跟随团体积极展开演艺活动,通过实战演练磨炼各项技能。但父亲希望她报考北京舞蹈学院的研究生,通过学校的正规教育提升能力后,再走向市场。在他看来,女团这个市场存在太多追求短期利益最大化的商人,满怀梦想的孩子们,在这样的市场中,可能会遭遇巨大的打击。“她们做的这件事需要社会的认可,如果社会反馈她们的不是想象的那样,受打击的是精神,这是很可怕的。” 如果在女团市场非常成熟的,这样的担忧或许是多虑的,比如在日本,女子偶像已经被视作一个全日制职业,拥有成熟的培训和评价体系,代表人物也具备一定的社会影响力。 AKB48在日本被称为“国民女团”,这个称号并不是个宣传噱头,在团体最鼎盛的时期,大街小巷的店面都放着她们的歌曲,成员们出现在各种知名品牌的广告里,在电视剧中则跟木村拓哉这样成名已久的前辈合作。可以说,AKB48的出现,扩展了人们对偶像影响力的想象。 困境 产业链完成度低、曝光机会少 但国内的市场并没做好准备。 女团的制造有两种模式,常见于韩国团体的练习生模式,经纪公司招募到一群成员后,进行长时间的封闭式训练,达到要求的成员将以组合的形式出道。公司会调动各种资源推广出道的团体,换言之,出道即成名。 这种模式的弊端是前期投入过大,一大批练习生最后能出道的寥寥无几。日本的女团则是另外一种运营模式,通过选拔招募一批成员后即可出道,通过线下剧场表演、巡回演唱会、参与综艺和电视剧拍摄等方式展开活动,成员的能力会在以演代练的过程中不断提升,这种模式可以更早地获得营收,这也是国内不少女团选择的模式。 但学习了日本模式的女团,不仅没有快速盈利,反而陷入了烧钱和亏损的困境。女团如雨后春笋般出现,辨识度却有限,真正获得大众认可的寥寥无几,2017年底,曾被重金打造的女团1931组合宣布解散,为女团的惨淡增加了一个无奈的注脚。 女团难以为继的背后,是产业链的缺失。音乐产业的不发达,大幅增加了女团的音乐创作成本。“国内好音乐人匮乏,想做一首精品的歌曲,只能花大价钱请顶尖音乐人或者海外音乐人制作,IdolSchool最贵的一首歌光成本就30万,同样的品质,日本的女团制作费用要低很多。”王一凡举例说。 链条上缺失的条块不仅仅是音乐,还有完善的曝光体系,音乐打歌节目的缺位使得大价钱做出的歌曲无法广泛传播。张展豪最头疼的一件事就是女团成员们缺乏曝光的平台,电视台和网站的主要综艺节目和电视剧中活跃的大多还是明星和演员,而女团成员中除了少数人气较高的头部成员能获得影视剧和综艺的青睐,大部分人只能通过经纪公司自制的网络节目和观众有限的剧场演出获得曝光。 谭妍喆是极创引力文化旗下女子组合加减乘除的成员,经历了一年多的培训之后,2017年正式出道。但她却说,走上女团这条路之后最迷茫的一段时间就是出道之后,“日子跟之前相比没有任何变化,开完发布会就结束了。” 产业链完成度低导致女团内容产出成本大幅增加,羸弱的版权保护机制和尚未成熟的粉丝群体则影响着收入。音乐版权是AKB48系团体重要的收入来源,她们的歌曲在KTV点唱度很高,每一次被点唱都会给团体带来版权收入。 日本的模式可以照搬,日本的粉丝却不能复制。纪录片《女团》的总导演刘柳提供了一种理解思路,相比日本,的宅男文化相对较弱,而宅男向来被认为是女团付费的主力人群。“日本是高度老龄化社会,很多年轻人其实也没有太多激情和梦想,贩卖梦想的偶像团体就是为了刺激他们产生欲望,但的年轻人不缺乏欲望和梦想。” 社会环境也会影响付费行为,通过购买音乐CD换取和偶像握手时间的“握手会”是AKB48系女团提振销量最有效的手段,但这种模式很难完全被社会接受。“一方面,体验型经济不够发达,另一方面,大家在观念层面也无法接受这种行为,你能接受男朋友每月去和小姑娘握手吗?”,王一凡说。 不论是男粉还是女粉,对于女团的要求会更苛刻些,他们希望看到成长、努力和敬业,这是付费的重要前提。影子曾经是SNH48的粉丝,饭了两年之后出坑。“成员们在第一次总选举(粉丝通过投票应援各自的偶像)之后心态变了很多,不关注如何在舞台上好好表演,反而更在意票数。”在为喜欢的成员投票上,影子并不吝啬,但打动他的还是成员为提升唱跳能力做出的努力,投票只是附属。“第一年唱跳都不好没关系,第二年还这样就说不过去了。” 未来 靠衍生品授权、代言变现 女团是门慢生意,认识到这个道理的从业者们开始安心回到自己的偶像事业中。 刘勇觉得,偶像归根到底是种叙事创作,要做好这件事,首先要遵循内容创作的规律和思路。在他看来,三种错误的思维正在主导着的内容产业,第一种是制造业思维,比如‘既然一个编剧写一个剧本要十个月,那十个编剧一个月能写完了’。第二种是投行思维,“在这种思维下文化是商品,是可以像炒股票一样炒作的概念,概念被炒火之后,从预期价值中盈利”。第三种是互联网思维,强调覆盖更广泛的受众,“用这种思维做内容会引来一大波的围观用户,但用户对平台没有情感。” “领先半步是先驱,领先一步是先烈”。王一凡引用了他在传媒大学读本科时任课老师张绍刚的一句话。王一凡最初做IdolSchool时,希望能把日系偶像制度完整地带入,经历过了产业不完善带来的困境后,他开始反思自己的运营模式,剧场模式曾经是日系女团模式的核心所在,现在他开始重新衡量运营剧场的性价比,寻找到适合市场的女团运营模式是当务之急。 适宜的女团运营模式已经在从业者们的实践中逐渐清晰起来:暂时放弃从大众手中赚钱,通过衍生品授权、代言等方式从商家和品牌处完成变现。刘勇正在为安菟接洽各种游戏、衍生品授权和品牌代言,王一凡和张展豪也积极跟品牌洽谈代言合作、广告片出演等等。在这种模式下,他们可以更安心地做好优质内容。 采写/新京报记者 王雪琦 |